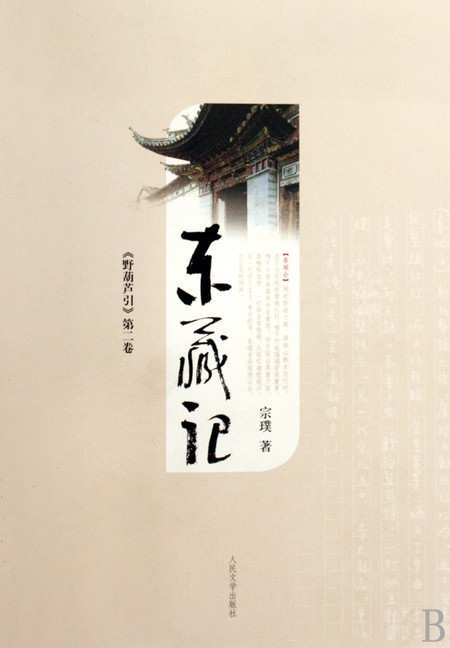 |
作品简介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99—2002)《东藏记》,是当代女作家宗璞创作的作品。《东藏记》是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二卷,并可独立成篇。这部作品描写明仑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樾教授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它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敌人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都在作品中得到深刻细腻的表现。 |
衣冠南渡,离人北归;失魂东藏,热血西征。
国在山河破,故园荒草深。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世间难有温情的烟火漫卷,人多是在飘零流落中,迷惘地寻找可以安放身心的所在。
时间倒带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一张血与火的大幕,在中华大地迅速铺展开来。
于抗战烽火之中,于流离失所之境,如何守护学人风骨,如何赓续国之文脉?
血色年代设问,西南联大作答。
1937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选择南渡西迁,师生兵分三路、水陆兼进,于1938年2月辗转迁至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是一所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时间存续仅8年,却被视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珠穆朗玛峰”,孕育出一个中国现代版“人类群星闪耀时”——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2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社会科学大师。
数字只是一种符号标志,其中的深层内涵,则是在艰难年代,知识分子依然坚持立德立言、无问西东,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坚守学人风骨、家国情怀。
读懂西南联大,既需要从历史记述中打捞细节,也需要通过社科研究进行探幽,但,最能触摸到其中人文底蕴的,还是细致入微的故事。
关于西南联大的文本叙事有很多,从华裔作家鹿桥的长篇小说《未央歌》,到汪曾祺系列散文《跑警报》《西南联大中文系》《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等作品,都为这段历史留下笔墨华章。
不过,能够透过历史迷雾,把那一代知识分子群像刻画得淋漓尽致,寻迹到那段历史深藏的命运暗示与时代玄机,娓娓道出那个年代个体生命成长与国家民族觉醒之间的相互律动,以强烈的在场感和人格化将那段岁月织成一幅历史画卷的,非宗璞的《野葫芦引》不可。
宗璞,生于书香世家,家学渊源极深。父亲冯友兰,学贯中西,是著名的哲学家。宗璞幼时生活的地方,就在水木清华、北大燕园。家学家传,往来鸿儒,都在宗璞内心植入深厚的传统文化因子。
宗璞作为南迁家庭的子女,四五岁时移居昆明,和大人们一起跑警报。在昆明街头,有时是闻一多拉着宗璞手逛来逛去;有时是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女士带着她,提篮走路去冠生园卖教授夫人们自制的点心。有很多个夜晚,她看着父亲冯友兰在小油灯下写作,满脸被油烟熏得黑乎乎的——冯友兰著名的《贞元六书》,就是出自这样的环境。
多年以后,这段岁月被宗璞用生命之水煮成文字,取名《野葫芦引》。这部小说共分《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4个部分。其中,第二部《东藏记》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东藏记》,即取“东躲西藏”之意。
救亡图存,大义大爱。对此,宗璞并没有选择宏大叙事,进行所谓的“史诗式”表达,而是以个人细微视角,带来一缕烛照,洞见历史文明。宗璞这样解释书名《野葫芦引》:“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我很同情它。但我写的又是小说,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不明所以的东西,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人其实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所以人生、历史都是‘野葫芦’,没办法弄得太清楚。那为什么是‘引’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百态。”
跟着宗璞,一起凝望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静水流深,深潭无波,在不知不觉中,人心就沉入到被岁月湮没的文化谷底。
宗璞语言清丽典雅,含蓄内敛,藏而不露,雍容和顺,婉约清新,既有明清小品的雅致,又有西方古典小说的静谧。她以绵密的文字、幽微的细节、严谨的叙事、深刻的愁思,展现出小说写作极高的艺术水准,给读者带来极致的审美价值体验。
当然,作为小说,《东藏记》并不具备多少“戏剧冲突”的特点,在情节设置上也缺少悬念,故事实在不够“抓人”,对缺乏耐心的读者来说,似乎并不“友好”。甚至,这样的作品也可以不叫小说,而是长篇叙事散文。小说中有很多章节,都可以独立成篇,当然,把“四记”联系起来,又能找到交叉联系和深层呼应之处。总之,宗璞将思想、人格、气质、才情深度糅合到一起,以温婉叙事,让人们看到那段历史的宽阔和深幽。
战争,只是这部小说的一个远景。作者铺陈的世界,仍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仍有瑰丽壮阔的山河,依旧太平的街市,淳朴新奇的民俗,情爱交缠的人生。比如,宗璞写“跑警报”,敌机只是路过未有屠戮时:“他们出了防空洞,见天空还是那样蓝,云彩还是那样飘逸,蜡梅还是那样馥郁”;空袭之后,叙事主体“嵋”被人从土中扒出时:“天还是那样蓝,那朵白云还在不经意地飘着。外公,警报,飞机,炸弹在她脑中闪过,她随即意识到,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
生者不言,死者默默。鲜血和热泪,永远不会被轻易湮没与遗忘。那些先“渡”后“藏”的知识分子,那些先“征”再“归”的热血儿女,命运轨迹都因战争而改变。特别是对那些出生高门世家、书香门第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成长经历,并不是什么血色浪漫,而是心灵磨砺。
作为一部刻画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像的作品,《东藏记》笔触聚焦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既在为大师巨匠们祛魅,也是在抚摸知识分子成长的复杂心路历程,还通过一些背离操守的知识分子,来思考人格和风骨在特殊环境下,如何坚守,为何沦陷。
孟樾、卫葑等传统知识分子,不论外部世界怎样风云变化,都能坚守中国士人的传统道德和人格操守,让人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能立得起来”的形象。孟樾是一位追求学术和关心国运的学者,他“沉稳坚定,既有传统文化修养,又具民主科学意识”“不畏当局的压力,排除流言的干扰,以爱国学者的良知,教书育人”。他潜心研究历史上几次“南渡”的深层原因,希望“以史为鉴”;撰写不少批评文章,痛斥当局腐败,勇敢直面现实。
这样的知识分子,既是先知的觉醒者,也是忧思的仁爱者,还代表着中国高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在小说中,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比如,卫葑品行端正,有君子之风;江昉豪放旷达,有大义之情;庄卣辰冷静沉着,视科研为生命……这些知识分子关注民族存亡,忧道不忧贫,绝不做有悖民族大义的事。比如,校长秦巽衡“声音呜咽,一字一字地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我们决不投降’”,不难看出,在艰难时代,总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节操气节,凛然长存。
当然,《东藏记》中也有一些有缺点的知识分子。比如,白礼文虽然学有专长,但太过慵懒,贪图享乐;钱明经特别擅于交际,但生性风流,势利冷漠。小说中还写到一对极为刻薄、迂腐庸俗的教授夫妇——尤甲仁、姚秋尔。这对夫妇喜欢互吹互捧。比如,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这对夫妇还热衷飞短流长,作者这样直斥:“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
学界普遍认为,尤甲仁和姚秋尔的原型,是钱钟书和杨绛。钱钟书在西南联大恃才傲物,言语刻薄,受到排斥后,很快待不下去,这些经历与尤甲仁、姚秋尔这对刻薄夫妻经历形成对应。值得一提的是,冯友兰、宗璞父女与钱钟书夫妻之间存在矛盾,双方打了多年笔墨官司。在小说中,宗璞将尤甲仁、姚秋尔夫妇放在“刻薄巷”,一改整部小说风格含蓄隽永的特点,以鲜见的嘲讽笔触,狠狠刻薄了一把“刻薄人”。历史的吊诡与现实的魔幻,尽显其中。
随着时间推移,晚年宗璞渐然从个人私怨走向时代反思,选择了和解。宗璞说:“我和杨绛先生之间的不愉快是时代的颠簸所致。”她还感叹:“南渡、东藏、西征、北归,人们回到了故土,却没有找到昔日的旧家园。”
弦歌不辍,芳华待灼。作为一部“向历史诉说”的作品,《东藏记》清晰地表明,哪怕是在特别不堪的年代,哪怕现实生活再过颠簸,也总有一群知识分子在捍卫着人格精神,沉淀着一种俗世稀缺的清贵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