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人物名片
余世存,作家、诗人、著名文化学者。1969年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近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人的时间文化,“时间之书”系列已成为百万级传统文化IP。已出版《非常道》《老子传》《家世》《自省之书》《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时间之书》等20余部专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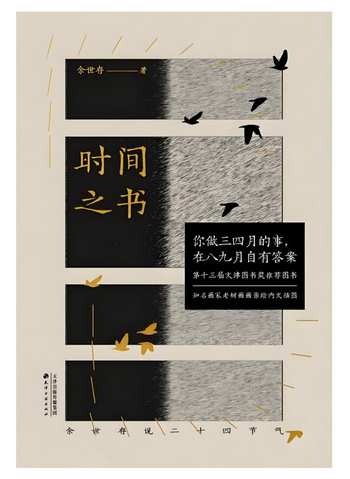 |
余世存著作。 |
 |
学生时代余世存(后排居中者)与同学在北大西门。(受访者供图) |
余世存瘦了。
跟此前他在各大媒体的照片和视频相比,眼前的他明显清瘦了许多,由内而外,透着一种风轻云淡的通透自在。他看上去很青春:一头利落短发,一件纯黑polo衫,这样的外形让56岁的他倍显年轻。当然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半框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清澈明亮,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文化学者、诗人、作家,身为当代文化界一位典型的“斜杠中年”,余世存身上有着众多标签。这些标签看上去有些一本正经,其实换一种思路,还能找到更文艺的表达,比如你可以向DeepSeek提问“余世存是谁”,经过一番思索,它会给你这样一些答案:“历史切片师”“时间诗人”“汉字守护者”等等。
但余世存本人却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喜欢读书,也读了不少书,还写了一些书,仅此而已。”他直言,甚至在45岁之前,自己还会为钱发愁,人生面临诸多挑战,“如今人生过半,我真的越来越找到了一种怡然自乐的舒适感,活得也越来越丰盛、轻盈。”
近日,应重庆市全民阅读品牌活动“陆海讲读堂”邀请,余世存作为第八期活动讲读人做客重庆。活动主题是讨论“节气时间的智慧和现代意义”,我们的对话却试图探寻另一种终极意义——人生的意义。
“我的经历或许对于今天的广大年轻朋友有所参考。”他坦诚地分享了自己一路成长的故事,“是阅读和写作让我这个曾经羞赧的自卑的普通人得以拥抱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年轻朋友们,不要焦虑,不要躺平,要勇敢追求,要始终相信,未来的美好人生,等着你去拥有。”
35年前毕业旅行来重庆
遭遇一场人生的自我拷问
新重庆-重庆日报:你是湖北人,重庆与湖北一衣带水,人文相亲,你对重庆有何印象?
余世存:我来过重庆好多次,很喜欢这里。在我心中,重庆是一座开放包容的现代化大都市,更是一座曾见证我思想转变的重要城市。我第一次来是1990年大学毕业那个夏天,我的毕业旅行目的地就是重庆。
我那次在重庆住了好几天,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挥之不去——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样的拷问,让那时年轻的我反复思索,甚至回到北京,还一直在想。
我最后的答案是,人作为一个个体,一定要在世俗生活中跟他的家人、朋友建立起爱的连接,这种连接会赋予他人生意义。只要有了爱,哪怕他就在一个小地方生活一辈子,没有去看外面的世界,没有跟几千公里外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关系,他的人生依然有意义,同样是重要的一生。
所以,如果说重庆给我最深的印象,那就是35年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在重庆遭遇的这样一场自我拷问:我们这些普通人,究竟应该怎么去赋予人生的意义。
新重庆-重庆日报:当时你大学刚毕业,对于未来有怎样的想象?
余世存:这就要提到我的同班同学伊文,他现在是你们重庆的一位媒体人,我们关系很好。我来重庆就住在他家,他带我去吃火锅,又带我去长江边,看滚滚长江东逝水,聊很长很长的天。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讲:“小余啊!你以后怎么打算啊?我们这些同学啊还是挺为你操心的。”
伊文的意思是,我太书生气了。他建议我应该回学校深造,继续读书,争取留校教书,他说我就是一个适合校园环境的读书人。这些话我听了特别感动,这么多年了,我跟伊文虽然山水相隔,但一直惺惺相惜。
同学们为我操心,我想可能是因为上大学时年纪在班里算小的,只有17岁。伊文他们都比我大一些,加上我是湖北小地方来的农村子弟,在这些城里来的同学面前,难免有一种自卑,显得木讷,沉默寡言。
说实话,我那时真的挺迷茫的,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一中教语文,身边鲜有志同道合者,心里是苦闷的。
我常常在课余时间泡北京市图书馆,白天读萨特,晚上写随笔,半年积累下十几万字。两年后,我便辞职下海了,后来又到《战略与管理》杂志任职,从编辑做到主编。直到2005年,我写出了《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这本书以《世说新语》式的笔记片段完成,非常畅销,我才慢慢地,在阅读写作这条路上了道。
曾是自卑的“小镇做题家”
与同窗合力推出《穆旦诗全集》
新重庆-重庆日报:但你当年也是随州文科状元考去北大的,没有一种天之骄子的骄傲吗?
余世存:没有,没有。实际上我一去北大就挨了一记闷棍,很长时间都在一种不自信的状态里。我可能在随州很优秀,但到了北大,跟全国的精英一比,才知道自己无论眼界和能力都差很多。
比如我去文学社报名的时候,学长让我写下最钦佩的作家的名字,我写的是鲁迅、闻一多,但那些大城市来的同学,写的都是乔伊斯、普鲁斯特。你能想象我的感受吗?这些名字我听都没听过。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时的我就是一个“小镇做题家”。
新重庆-重庆日报:这种不自信的状态是如何改变的?
余世存:还是靠多读书。记得我当时的英语老师是俞敏洪的同学,老师劝我少读中文系的书,多读点哲学、美学,后来我的阅读视野慢慢地打开了,信心又重新拾起来了,所以读书一定要文史哲贯通。
好在我们那时候校园里的读书氛围非常浓,同学们也爱交流碰撞,后来还真的弄出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今年高考语文科目的作文题涉及了穆旦的诗,其实穆旦的重新发现就跟我们这批爱读书的北大同学有关。
新重庆-重庆日报:如何来理解穆旦的重新发现跟你们这批同学有关?
余世存:我们上大学时,我的同学文钊在图书馆读到穆旦过去的诗歌,非常喜欢,他把图书馆里能找到的穆旦诗歌全部抄下来,整整两大本。我借过来看,很快就熟读会背了。
我们笃定穆旦非常重要,他的诗歌成就不亚于戴望舒、徐志摩这些大诗人。所以尽管当时穆旦在社会上知道的人很少,但凭着我们心里对语言的把握和感觉,我们认定我们是跟这样的精神血脉连在一起的。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一中,文钊分到中国文学出版社当编辑,他在选编“20世纪桂冠诗丛”的时候,只选了三个人,里尔克、瓦雷里和穆旦。他把我们这帮同学,包括西渡、臧力、橡子等拉去做编委,相当于我们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共同努力,把这个诗丛选编出来。其中的《穆旦诗全集》,是国内第一次出版的穆旦诗歌全集,成为后来的穆旦研究者绕不过去的一个参考文本。
所以,穆旦在上世纪90年代被重新发现,离不开我们北大同学以学院派的形式推出这本诗全集,从那时起,穆旦迅速地广为人知了。
喜欢穆旦,也为年轻时常常苦闷的我推开了一扇门。有一次在新街口等公交车,偶遇“九叶派”诗人郑敏的女儿,我们聊起来,我说我喜欢穆旦,她问,你喜欢穆旦的哪一句诗?结果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出了自己喜欢的那句诗,竟然是一样的:“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人的生活。”当时这句诗对我们的触动都特别大,尤其在我看来,这更是一句帮助一个年轻人走向成熟的诗。
后来我在《中国人的家风》里面也写到了穆旦家族。今年高考穆旦成为热词,好多媒体说我押中了作文题,其实不是我押中的,而是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一直在读穆旦,一直在跟他进行精神对话。
新重庆-重庆日报:回顾你的写作,在2005年《非常道》大获成功后,很快回归原典,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智慧和力量,为什么会转变?
余世存:大学时代我的阅读写作受西方影响很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些忽视。后来,意识到自己知识谱系里在传统文化方面有缺失,我就开始不断回望传统挖掘宝藏,我借此滋养自己,也滋养更多读者。
对我来讲,后来对于传统文化的补课,还有些歪打正着。如果我很早就在传统里“浸泡”,那么我很可能没有现在这样的分析认知视角,正因为我一开始不在里面,是后来从外面进入的,我才可能对传统的认知和理解更客观一些。
45岁前都为生计发愁
内心的追求一定要坚守
新重庆-重庆日报:当今社会年轻人普遍感觉压力大,你认为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现实的种种挑战?
余世存:我当年压力也很大呀。我主动脱离体制时,好多同学都担心我要饿死。事实上我这种为生计发愁的惶恐感,在45岁之前就没有消失过。真的,很长一段时间,现实的挑战对我而言都是家常便饭。所以,我想我的经验对年轻朋友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你不能说,一个义无反顾选择追求理想的人就一门心思全是理想,现实生活中他该发愁还是要发愁,但光发愁没用,还得回到内心世界去。对于我,这样的世界就是去处理文字,处理人类思想相关命题,这才是我该做的工作。
我从来不觉得,做工作就羞于谈钱。年轻朋友一方面要学好赚钱的本领,这是活在世上的物质基础;另外一方面,也绝对不能放弃自己内心的真正的追求,处理好月亮和六便士的关系,真正的追求,一定要坚守。
这好像也是我第一次跟记者谈到这一点。坦白说,我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为钱发愁,甚至我专属的书房都是八九年前才拥有的。很多年轻朋友对此甚至难以置信,哦,原来老余奋斗了这么久,才拥有了毕业之后一直都想要的一间书房?这个事实也让他们感到释然,在面临一些现实问题时,心态放平了,不那么焦虑了。
新重庆-重庆日报:你最困难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
余世存:应该是我写《老子传》的时候,2009年的夏天,我40岁,像流浪者一样,我在贵州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了黑塞的《悉达多:流浪者之歌》,我觉得我也能写中国的《流浪者》,那么我就来写老子。那年秋天,我又去了杭州,住在另一个朋友家里,他家在临安,太湖源头的一个村子,有一大片竹林,我就在那个村子写完了初稿,那时我真没有钱,就靠去朋友家蹭吃蹭住,以前我在北京也是靠给朋友的杂志报纸写专栏度日。
新重庆-重庆日报:如此艰难为何没去找一份工作?
余世存:我毕业后先是教书,后来去做杂志,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我要用自己的才华和所学打拼自己的事业。其实在那之前,我对未来要做什么还有一个很大的构想,比如我曾想做类似于法兰西学院那样的机构,我甚至还做过一个“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我知道我的很多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我就欠缺一种落地转化的商业能力。
新重庆-重庆日报:在流浪中坚守,让我想起你的忘年交、学者舒芜先生,他抗战时在重庆也曾有过类似经历。
余世存:对,对。舒先生给我讲过,抗战时他作为流亡学生来到重庆上学,常常在重庆的书店里面站着读书,那段经历是他人生中重要的印记。他记得当时书店总是挤满了流亡学生,书店工作人员也非常好,从来不赶他们,他们今天去读一段,记住页码明天过来继续读。生活很困窘,穷得每天只能用酱油泡饭吃,吃一碗酱油饭,头发一两个月都不理,长得要命。就这样子,他们还是坚持跑到书店里面看书,心中有梦,只为救亡图存。
舒先生给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也是我在北京刚工作很迷茫的时候,他让我觉得找到了同道的感觉。我进而想到,为什么他们当时如此艰难还坚持读书、甘之如饴,一方面是为中华之崛起,更重要还在于他在那些同龄人里看到了同类,我觉得这就是吾道不孤,互相鼓舞。
我想这种阅读是年轻朋友应该具有的一种生存状态,哪怕现实生活有难处,也要如饥似渴地去阅读、去学习,书中不一定有答案,但一定会在某个时刻,让你感到光明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