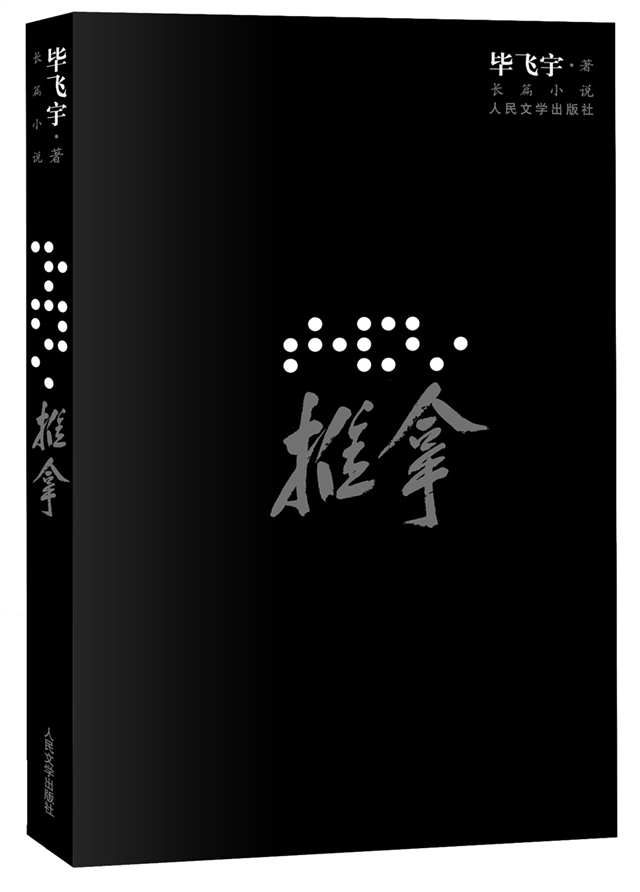 |
作品简介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07—2010)《推拿》是当代作家毕飞宇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近18万字的小说讲述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这也是国内少有的以盲人群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本着对盲人群体最大的尊重与理解,描述了一群盲人按摩师独特的生活,细微而彻底,真正深入到了这部分人群的心灵。小说以很小的切口入手,以“沙宗琪推拿中心”里的一群盲人的生活为中心,去触摸属于黑暗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并对盲人独特的生活进行了透彻、全面的把握。 |
黑暗世界,边缘人生;创伤隐痛,守护尊严。
人间不值,人间失格,这两个热词,常被用来感叹对社会和人生的失望。不可否认,现实之中确有命运不济和社会不公,让生命难以承受生活之重。
不过,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真正被生活热爱。人间烟火漫卷,红尘恋恋不舍,那是因为生活多彩多姿,生命极为深刻。人间值得,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光,看到色彩,走向有光的所在,拥抱五彩斑斓的生活。
有些人,就生活在无边的黑暗里,命运随时被抛在某个边缘地带,生活常处在无尽疼痛之中。谁给他们生命之光、社会温暖和精神治愈?
作家毕飞宇的《推拿》,就是在关注盲人群体,透视那个没有光的世界,来求解被黑暗遮蔽的人生难题。
小说家毕飞宇,能满足人们对文人作家的所有期待和无限想象。如果“江南才子”这样旧式文人身份用起来不显流俗的话,那毕飞宇无疑就是最为与之适配的。南京是一个极具文化江南气息的所在,毕飞宇、苏童在这里吸纳了江南古典的气韵气度,不论是形貌气质还是作品价值,都是那么美好,那么深刻。
在《推拿》之前,毕飞宇的《玉米》《青衣》《平原》等作品,就有着浓郁的古典气息,仿佛每个字句都被传统文化浸染过。而到《推拿》则不一样了,毕飞宇一头扎进了盲人狭窄逼仄的黑暗世界,以压抑的笔调,探照着人性的幽暗,叩问着世道人心,展现出作家“介入现实”的强烈批判意识。
《推拿》获得茅奖,本身就是国家文学奖评选的一次价值升级。它意味着,文学价值不必完全体现在宏大叙事上,文学表达也不必都追求所谓的史诗式呈现,好的作品也未必一定要打着鲜明的主旋律烙印,只要真正回到文学的轨道上书写真实生活,哪怕是聚焦边缘地带,只要能引发反思和改变,就同样能获得国家文学荣誉的垂青。
毕飞宇曾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任教,对盲人心理特性自然有所研判。后来,他因伏案写作导致身体劳损,到盲人推拿中心进行治疗,与盲人有了近距离的频繁交往,进而更加了解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由此,他用《推拿》打开一扇通往黑暗世界的窗口,让人们感受到盲人承受的隐秘疼痛。
从这个意义讲,《推拿》并不只是在写盲人,而是在通过盲人之眼和人类社会进行灵魂对望,来展示盲人“边缘社会”与“健全人主流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正如余秀华用诗歌的批判力量,证明脑残比脑瘫更丑陋可怕,毕飞宇用小说的反思精神,证明了心盲比眼盲更无知危险。
真正一流的小说家写作是难以被定义的。对毕飞宇小说的文本和结构,如果简单地套上某个理论框架,其实很容易陷入尴尬的错位。《推拿》就是这样的作品,全书除了开头的引言和尾声,每个章节都是以人物命名,以一幅幅盲人浮世绘来展露他们隐秘的心理历程。只有成熟的小说家,才能完成这种层层叠加的“心理叙事”潜性结构。
当然,毕飞宇小说最具魅力的,是语言铺陈。他的文字是内敛的,又是奇瑰的;是隐忍的,又是锐利的;是绵密的,又是简洁的。《推拿》里的字句辞章,就像是附在通往盲人黑暗世界道路边上的萤火虫,是发光的,是体贴的,是精准的,是有生命的,映照着一条条狭窄的通道,让我们跟着盲人,走向他们惊心动魄又波澜壮阔的世界。
比如,毕飞宇这样描述失明的痛苦:“后天性的盲人必须要做一件事,杀人。他必须把自己杀死。这杀人不是用刀,不是用枪,是用火,必须在熊熊烈火中翻腾。他必须闻到自身烤肉的气味。什么叫凤凰涅槃?凤凰涅槃就是你得先用火把自己烧死。”这样的句子,让一种绵绵不绝的隐痛,从纸面传递到读者指尖,顺着经脉,直抵心尖,成为一根坚硬的刺,深深地扎进去,带来强烈的悸痛。
这样的语言极其复杂,又极具辨识度,体现了无与伦比的智性与想象。这不是训练形成的手艺,而是天赋的才情。面对这样极具才华和想象的语言表达,任何模仿复述都会有强烈的挫败感。正因如此,《推拿》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电视剧,虽然也很火,但一千个导演,一万个编剧,都无法还原毕飞宇以文字呈现的心理细节和反思力量。
在《推拿》中,毕飞宇狠狠嘲讽了现实社会对待盲人群体的轻慢、歧视和掠夺。健全人经常对残疾人说,你们要“自食其力”,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似乎只有残疾人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就可以淡定地啃老,从容地躺平。那种以优越者自居的心态,那种以施舍者自居的同情,对盲人造成的心理伤害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推拿》里的王大夫,天生全盲,父母把万千宠爱给了健全的弟弟。王大夫勤苦自立,而弟弟则成了一个好吃懒做、冷漠自私的赌鬼,是一个只知道无限索取的“活老鬼”。王大夫挣的血汗钱,本是想给自己办一场简单有爱的婚礼,开一个让妻子成为老板娘的推拿房,然而,为了给弟弟还赌债,他只能用自己的鲜血来还弟弟欠下的债务。最令人心塞的是,王大夫给了弟弟两万元婚礼钱,弟弟却嫌弃他的盲人形象丢人,连他到婚礼现场的资格都给剥夺了。
这种被掠夺被侮辱被损害的残酷人生,在《推拿》里几乎无处不在。
张宗琪的父亲后来找了个女人,这个恶毒的后妈对他说:“小瞎子,你要是乱说,能毒死你,你信不信?”从此,张宗琪再也不敢和做饭的女人说话了,过度防范也让他失去原本可以得到的爱;在推拿中心,高唯是前台接待,不是盲人。她表面真诚热情,其实极有城府,她所有的友善不过就是为了谋取私利,不过就是为了实施自己的掠夺和报复。
都红,人长得很美,从小极具音乐天赋。她在慈善晚会上弹琴,因太过紧张乱了节奏发挥失常。这时,主持人煽情地赞美她是“为了回报社会”,鼓动人们给予她怜悯的掌声。都红意识到,慈善演出“就是把残疾人拉出来让身体健全的人感动”,意识到自己只是换取募捐的棋子,就再也不碰钢琴了。在推拿室,客人讲各种荤段子,污浊、肮脏、龌龊、下流。对此,都红只能沉默。
毕飞宇写道:“在公众面前,盲人大多都沉默。”“后天盲人的沉默才更像沉默。仿佛没有内容,其实容纳了太多的呼天抢地和艰苦卓绝。”小马就是一个后天盲人,他为失明自杀过,脖子上留下深深划痕。最终,他选择沉默,每天都在听时钟的“咔嚓”声。这种沉默,就是对痛苦绝望的忍受和消解。在黑暗世界中,盲人用沉默抵抗着尖锐的疼痛,而这些疼痛往往正是来自所谓光明地带的人们。
认识了黑暗,才能读懂世界上所有的颜色。在浓厚的黑暗之中,有人可以把光明完整地送给你;日丽风和的现实之中,有人可能用黑暗将你笼罩得不见一丝光隙。在盲人世界的“黑暗”中,也可以看到爱与美,感受尊严与无畏;在繁华盛世的光亮中,也能够看见脏与丑,见证卑劣与怯弱。
盲人世界的“边缘社会”和健全人的“主流社会”,到底哪里才是光明的,哪里才是黑暗的,很多时候,就处于交错纠葛状态。正如毕飞宇在书中说:“这世界有人眼盲,有人心盲,眼盲的人可以用心去感受,心盲的人有眼也是摆设。”
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深情表达,如果她能拥有三天光明,她希望能够看到“人”,看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世界,读懂自然和艺术的博大灵魂。盲人在黑暗里苦苦寻找光明,健全人却在光明世界制造黑暗。这说明,黑暗与光明,并不仅是由光影造成的,而是被心墙隔离出来的。
来此人间一趟,都想光芒万丈。一个失去悲悯和良知的社会注定没有光亮,一个轻易就踩踏弱者尊严的族群只会泯灭人性之光。不论身处哪种地带,都应把光明完整地还给每个人,让人们一起走进有光的世界。这种光,就是毕飞宇在新作《欢迎来到人间》中所说的那种“只有被拯救的人才会有的光,是大幸福,大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