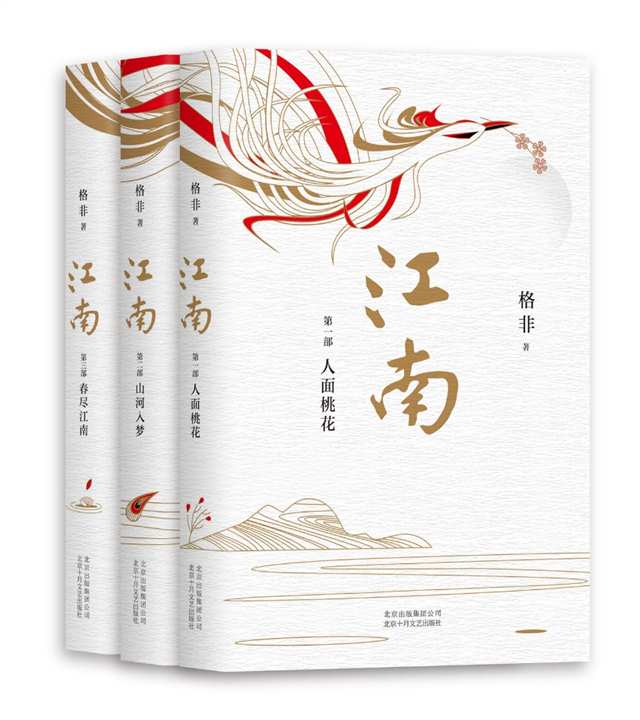 |
作品简介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江南三部曲》(2011-2014),是作家格非创作的长篇小说,包括《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部作品。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对历史和现实郑重负责的态度,深切注视着现代中国的壮阔历程。以百年的跨度,在革命史与精神史的映照中,处理了一系列重要的现代性命题。三代人的上下求索,交织着解放的渴望和梦想的激情,在兴衰成败与悲欢离合之间。 |
题记:江南残梦,历史宿命;精神重建,个人实现。
能不忆江南?何处是江南?
这样的感怀与追寻,之所以长久地交织于无数人心中,那是因为,江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种历史记忆,是一种文化概念,是一种心理意象,是一种价值判断。
江南秩序,江南文化,江南气质,江南腔调……这一切,都让人觉得,理想的乌托邦、梦中的桃花源,最适合在江南安放。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江南和桃源梦,是具象和抽象的互文。
只是,梦醒时分,遇见真江南之后,又总会面对太多的灰暗与浮躁,让人不经意间就从诗意跌落到失意。
文学里的江南,往往要比现实世界更加开阔,更有纵深,更为密实。读懂江南,可以从魏晋六朝以来淡雅婉约的诗词中寻迹,也可以从明清两代性灵的小品文中透视。当然,越过古典来到现代,江南的地理印象也越发清晰,可以跟着俞平伯去看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随着苏童去逛那条暗影斑驳的香椿树街,沿着叶兆言写的江南旧事去打捞历史的老物件。
不过,要祛除笼罩在“江南”这个文化概念上的迷雾,则需要跳出这些自然景观和物质器具,以更加开放的全球化视野来审视江南的时代性格。对此,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无疑提供了更好的镜鉴。
“江南三部曲”分三部,即《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格非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酝酿构思,随后,静心沉潜,精耕细作,于2004年出版《人面桃花》,2007年出版《山河入梦》,2011年出版《春尽江南》。2012年4月,历时十几年,完整的“江南三部曲”终于面世。这三部作品,各自独立成书,人物和地理又有着一定的线索连接,由此,历史命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思考闭环。
格非是个学者型作家,是先锋派的代表人物,既有灵思飞扬的才情,又有系统深刻的思想。显然,面对“江南三部曲”这样蕴藏着深厚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的作品,要成为其理想读者,就必须要跨越一定的文化思想门槛。
当下文学评论有两种声响,一种是学院派在玩弄晦涩难懂的概念符号,不加节制地贡献媚语口红;一种是所谓民间独立批评者极尽刻薄之能事,抛开文本、结构、思想的系统性分析,简单围绕那些具有感官刺激的描写进行讽刺谩骂。特别是个别自以为是的野生文艺评论家,以“骂遍”名家的方式招摇过市、博得薄名,其实就是在制造文化戾气。比如,有人就专挑名家作品中的性描写,对包括莫言、贾平凹、乔叶等人极尽嘲讽。这一点,格非和他的“江南三部曲”也同样难逃厄运。这种文化心胸格局,窄了,小了。
“江南三部曲”能以票数第一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本质上还是因为其中包含着值得信赖的艺术价值。近几届茅奖评选实行打分制,给这项文学评奖赋予了较为厚实的“民主评议”特质。从整体获奖作品的质量基本面来看,几乎不再出现前几届那种吊诡的评选结果了。诸如《都市风流》《骚动之秋》等后来几乎不再被读者记忆的茅奖作品,如今追溯到评奖环节,都能看到一些踩踏“程序正义”的人为干预。而随着评奖机制的日趋完善,随着文艺价值次序选择更具共识性,对待茅奖这种代表着国家最高文学荣誉的作品,读者当然需要摒弃浮躁、心怀敬畏,这本身也是应有的文化自觉。
独立批判是高贵的品质,但把刻意标新立异的哗众取宠,甚至是恶意攻击也说成是文学批评,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悲剧了。格非能把文学叙事和哲学思考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对“江南”的精神内涵和现实秩序进行更有体系性和逻辑性的思考,这样的文艺价值,当然不应被轻慢与亵渎。
语言是作家和作品的脸面,也是气质。凡是一流的小说家,首先应该是个语言学家。在茅奖作家中,作品的高度虽然不能完全与文笔划上等号,但好作品在文本与艺术上,一定都在某个高位达到平衡。莫言、迟子建、宗璞、陈忠实、苏童、毕飞宇、格非、徐则臣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莫不如此。经过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写作实践的格非,其语言风格是古典的,是诗性的,是有书卷气的,是充满意象的,是有抒情性的,是有音乐节奏感的。当然,格非语言也无处不在地充满哲思性。这样的小说,是留白的,是耐读的,是有带入感的。格非就是在用充满美感神韵的文本,养护他笔下的“江南气质”。
“江南三部曲”书写的是在“大历史”的转折点,个人在实现生命价值时遭遇的困境,来引导人们关于世界观、历史观、生命观、生活观的深刻思考。
从人物关系角度看,“江南三部曲”写了一个家庭近百年的“秘史”;从故事地点看,“普济”“梅城”“花家舍”等江南地理的安放地,被格非用来作为江南的表征。从时间内容看,《人面桃花》主要写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知识人群的人间桃花源情结,以及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探索追求;《山河入梦》集中在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权力阶层开启的那场具有“乌托邦”式色彩的社会实践;《春尽江南》则是聚焦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社会发展,来透析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江南三部曲,百年沉浮梦。《人面桃花》展示的是一个恍惚迷离的江南,《山河入梦》揭示的是一个疯狂失序的江南,《春尽江南》描写的是一个颓废绝望的江南。这样的江南诗意消亡历程,无疑正是在沿袭着以江南士人精神为代表的“道统”溃败、士人风骨沦陷的文化脉络,最终将历史浓缩于一个家族的百年命运变化,来铺陈一部古典诗意江南的现代颓败凋零史,让人们听到一曲关于文化江南生命消解的挽歌。
在《人面桃花》中,无论是陆侃为建设世界桃源的梦想发疯,还是土匪头子王观澄建成人间桃花源的突兀,抑或是张季元、陆秀米等中国第一代革命者建设理想社会的幻灭,都清晰表明那个时代的江南情结,只剩下了执念或私心。在《山河入梦》中,郭从年建立的花家舍,具有乌托邦式的美好表象,但这里的“大同世界”实质是由专制集权的威压来完成的。“花家舍人民公社”看似人人平等,其实人人自危,除了强权不受监督,普通人只能处于无孔不入的监视之中。试图革除制度弊端的县长谭功达,最终也只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作为“江南三部曲”的终结篇,《春尽江南》展示的则是现代欲望社会的秩序紊乱和人性迷失,主人公庞家玉从单纯的诗歌爱好者转身为逐利的律师,甚至在解决自身房产纠纷时还选择动用“黑社会”力量,在欲望包裹之中逐渐背离了良心与爱心。人性、文明、法治的沦丧,让江南再无春日,让精神家园走向荒芜。
花家舍,是三部作品中都写到的地点。在《人面桃花》中,花家舍是桃源图、桃源梦的实验田,是追求大同世界的理想主义者的集散地,是超越身份鸿沟有着共同生活愿景者的灵魂栖息地。那样的花家舍,只是活在古典残梦之中;到了《山河入梦》里面,在大历史的风浪冲击下,这样的“江南遗梦”渐然被惊醒了、刺破了、清洗了,制度变革的冲击力瞬间荡涤掉传统的人性伦理;最终在《春尽江南》里,花家舍在利益驱动下,陷入疯狂开发的物质洪流中,曾经的传统江南变成了一个表象繁华的灯红酒绿地带。至此,当年陆侃想把各家各户连接在一起的风雨长廊,经历了近百年的岁月烟云后,也彻底失去作为文明价值观的纽带价值,只能充当花家舍吸引游客的逐利工具。古典的文化江南,就如同这三部作品的三位女主人公——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在默然中香消玉殒,缓缓走向历史的尽头。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能不忆江南”,真正的好江南,一定不只是好风景。“何处是江南”,这样的无奈慨叹,更不会只是因为江南春色难觅的遗憾,而是对历史、社会、生命等社会哲学问题的现实求解,陷入了长久的困境。桃花源和乌托邦,都只是南柯一梦。真正的美好社会,依然未能成为被所有人都清晰看见的现实图景。在“大历史”的转折年代风雨中,如何实现个人价值,需要呈现更为理性的时代答卷。
人面桃花,历史残梦;山河入梦,不见自我;春尽江南,失魂落魄。在谈论江南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只是在谈论风景;在怀念江南的时候,人们都应该知道要怀念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