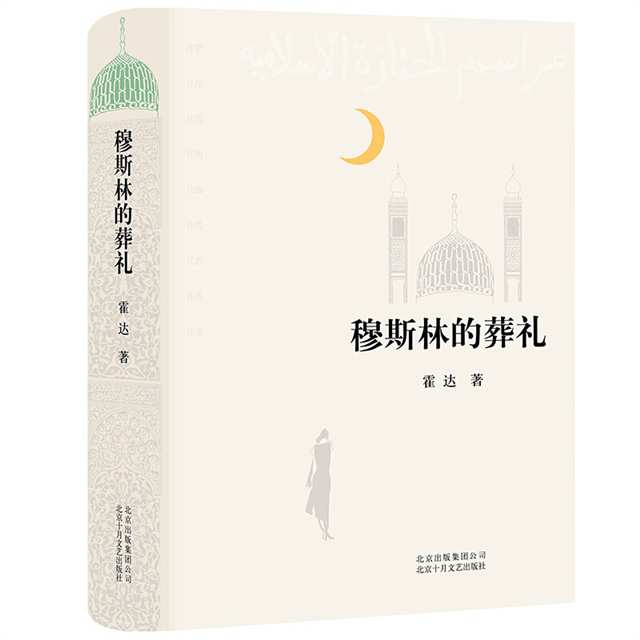 |
作品简介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85—1988)《穆斯林的葬礼》,为当代作家霍达所著。它是一部以回族手工匠人梁亦清的玉器作坊奇珍斋的升沉起伏为主线,跨越60年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梁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展现了穆斯林文化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独特风貌和深厚底蕴。小说中,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贯穿始终,让读者在感受家族兴衰的同时,也深刻体会到爱情、信仰、家族、生命等主题的复杂与深刻。 |
题记:雁归潮来,玉碎月残;爱情挽歌,圣洁诗篇。
人是万物之灵,是高级生物。这里的性灵和高级,是在指向情感和智慧。人类有丰富的情感,但不是所有情感都是高贵的;人类也确实很聪明,但并不是所有聪明都叫智慧。
爱情是人类最圣洁的情感,很多时候却被世俗观念吞没了;宽仁是人类必须的品质,很多时候却被功利欲望侵蚀了。爱得荒唐,死得潦草,如此庸常的生命状态,就是在书写人间不值。
爱情的高洁,死亡的价值,有时在现实中难以体验和提炼,那不妨到文学世界来感知吧。比如,读《穆斯林的葬礼》。因为这部小说是“圣洁的诗篇”,在“唱出一曲人生的咏叹”。如此审美价值,源于作家霍达的才情和努力。她曾这样表达这部小说:“把爱和死写到极致。”
作者写到极致,读者才能领略到爱的极致之美,感受到死的极致之痛。年轻时读《穆斯林的葬礼》,可能觉得这只是“才子佳人”故事,只是“纯洁凄美”的古典爱情。年岁渐长,再读此书,就会觉得这书是在写被时代洪流冲走的自我,在写被庸常生活辜负的爱与信仰。这是爱情之书,更是生命之歌。
有人说,《穆斯林的葬礼》是中国当代最有人缘、最纯净的书。在各种平台上,有大量读者对这部小说进行评论,说得最多的是“看哭了”。
泪水是有重量的,泪水也是有深度的。这样的阅读之泪,有少年情怀的清泪,也有岁月沧桑的浊泪。读这本书,信仰的力量带来的感动,总是那么真、那么深。
“爱情,是一种信仰”,小说中楚雁潮这样说。人活一世,总会尝尽悲欢。有一种众生迷茫,是我们的爱到哪里去了;有一种公共悲伤,是高贵的爱情变得满目疮痍。
荒芜乡村,欲望都市,指向的不应只是经济民生,还有情感文化。再美丽的田园,没有真爱也还是荒凉的,再繁华的都市,缺乏真情仍是冰冷的。当人性情感在利益裹挟和欲望吞噬中渐然消隐弱化,爱情就会渐然失去高贵的底色。
越是在真爱稀薄的年代,越要重新固化人们对爱情的信仰。《穆斯林的葬礼》是一个文化入口,可以打开一条通往高贵爱情之路,让人们在诱惑满满的年代,懂得选择在共同的价值理想轨道上,从相知走向真爱。
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穆斯林的葬礼》,在艺术表达创新上,至今仍然释放着独特的魅力。这部小说不论是叙事视角的切入,还是清澈精炼的文本,抑或是深沉绵长的情感,还有匠心独运的意象,都展现出经典文学作品极高的水准。正是因为饱满而又独特的艺术张力,这部作品才会被读者持久喜欢。
在叙事构架上,《穆斯林的葬礼》是有创新开拓价值的。小说整体由序曲、尾声以及正文十五章构成,通过奇数章与偶数章来形成两条叙事线索,以“玉”和“月”作为意象来对应韩子奇与韩新月父女两代人的故事,两条时空线索在平行推进过程中形成交叉点。同时,作者通过倒叙和插叙,不断切换岁月场景。如此结构,既新颖,又紧凑,也便于设置悬念。
新月难满,美玉残缺。这部小说以“月”和“玉”为意象,和小说人物的性格命运形成贴切的对应,可谓是极具匠心。韩新月清新脱俗、纯真善良、热情向上,但困于家庭伦理,遭受命运摆布,陷入情感与疾病的痛苦折磨,带着遗憾早早离开了人世;梁冰玉冰清玉洁、超凡脱俗、独立自由,但陷于宗教制约,被迫弃子漂零,多年流落异乡。“月”代表阴晴不定、变化莫测,“玉”代表圣洁纯粹、冰冷孤独。梁冰玉和韩新月是母女,“玉中有月,月中有玉”,这种实物意象带来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将小说的艺术水准提升到一个高度。
霍达曾说:“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的撞击和融合,这种撞击和融合都是痛苦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主公人韩子奇的痛苦人生根源。韩子奇跟着老人吐罗耶定走上朝圣之路,后被做玉器的梁上清收养。他既恪守着伊斯兰文化,也汲取了汉文化,后来结识英国商人沙蒙·亨特先生,接触到更为开放的西方现代文明。作为梁上清唯一的徒弟,为复兴“奇珍斋”,韩子奇与师妹梁君璧结为夫妻,既有报恩考虑,也有感情因素。这样的婚姻,既要遵循伊斯兰教规,又要恪守传统伦理道德,还要面对时代动荡的冲击,这一切,都为后来的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
爱情是需要被激发和唤醒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护玉器不被掠夺,韩子奇到英国避难,同行的有梁君璧妹妹梁冰玉。后来,伦敦陷入战火,异国生活充满绝望。在血与火的日子里,梁冰玉炽热的爱,终于让韩子奇内心沉寂的爱苏醒了。梁冰玉独立、开放、知性,爱情让他们生命绽放出灿烂光芒。十年之后,亲情和责任将他们生活拉回到从前。当韩子奇和梁冰玉携带女儿梁新月回到朝思暮想的家,梁君璧的反击和报复开始了。
一边是责任,一边是爱情;一边是家族,一边是信仰。伊斯兰教教义禁止娶两姐妹,韩子奇的懦弱和沉默伤透了梁冰玉,让她弃夫失女,孤独而去。这个走向觉醒的女性发出这样控诉:“我是一个人,独立的人……不是你们可以任意摆布的棋子!女人也有尊严,女人也有人格。”长大后的韩新月,长期活在“母亲”梁君璧的蛮横霸道阴影中。
高贵的爱情,有时就是对苦难生命的救赎。韩新月到北大上学后,从家族压抑的环境中走出来,不幸的是,很快又被查出患有严重心脏病。在生命危难关头,楚雁潮的爱与呵护成为支撑着她活下去的最后力量。但,这份高贵的爱情还是遭到梁君璧这个极端宗教主义信奉者阻拦。韩新月是回族人,楚雁潮是汉族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不可以迎娶或者嫁给一个非伊斯兰教的人。在梁君璧的打击下,失去爱情这样的信仰支撑,韩新月很快离开了人世,留给人间是一场悲伤的“穆斯林的葬礼”。
梁君璧的蛮横、独断、自私、任性,制造出太多悲剧。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源。梁君璧背负着生活之苦,经历过离亲之痛,丈夫韩子奇在临死前说出自己不是穆斯林而是汉人,让她又遭受信仰之灭。如此复杂悲剧人物产生,既要从历史时代进行追根溯源,又要从宗教文化进行分析梳理,还要以现代文明进行审视判断。
没有人可以活在真空中,政治、商业、战争、文化等等因素都是随时改变人生的变量,也是冲击一个人美好情感品性的要素。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梁君璧是宗教主义的工具人,韩子奇因对玉的痴迷失去自我,谢秋思因父亲是上海大资本家而遭遇身份歧视……人活一生,总会遇到各种不可抗拒的外力,这时候就需要像梁冰玉对女儿韩新月期望的那样,“有一颗坚强的心,在布满迷雾的人生中能牢牢地把握自己的命运,闯过一道道的难关” 。
“穆斯林的葬礼”包含着深层的隐喻。神圣、纯洁、庄严的葬礼,不只是生命的葬礼,也是家族的葬礼,还是爱情的葬礼。小说多次描写穆斯林人物的葬礼细节。不仅写葬礼,还写到婚礼。比如,对韩子奇和韩天星父子各自的婚礼就进行了细节呈现。这两段婚姻是在责任捆绑下举行的,这样无爱支撑的婚礼,无异于一种葬礼。韩子奇和梁冰玉生死相恋从未有过婚礼,韩新月和楚雁潮为真爱活着也没有仪式。可以说,“葬礼”和“婚礼”的价值反差,让“穆斯林的葬礼”传递出深刻的思想内涵。
“穆斯林的葬礼”是信仰者的虔诚,也是教条者的殉葬。很多现代人过着没有宗教的人生,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选择,也同样面临着融合和碰撞的痛苦。唯有文化开放,唯有价值包容,才能让人类可以守护高级的情感,让生命免于走向庸常贫乏。正如霍达所说:“我认为应该把宗教当成一种文化,宗教信仰应该是奉献,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只拘泥于形式。”
哪怕尝尽悲欢,也不能永失我爱。霍达也这样感叹:“我觉得人生在世应该做那样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剧,悲剧,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完成了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对自己心灵的冶炼过程,他毕竟经历了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高洁、纯净的意境。人应该是这样的大写的人。”
雁归潮来,玉碎月残。大雁失偶的悲鸣最是凄惨,潮来潮往淹没过多少无情岁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不忍直视的命运残酷,冷月无声残月清冷地掩映着太多的人生寒凉。
别再让原本高贵的爱情变得满目疮痍,别再让已经相爱的人们走向劳燕分飞。
